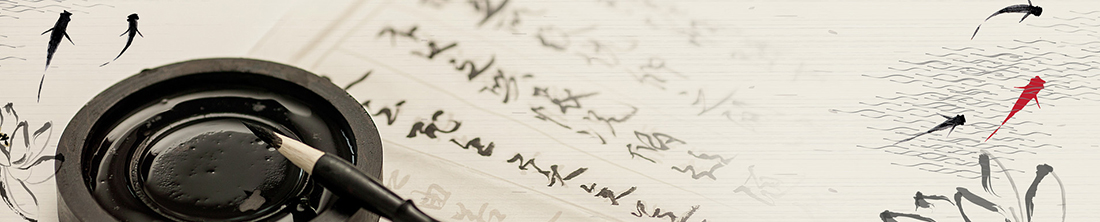
时代意义、父亲形象与疾病隐喻——看丁玲小说莎菲型女士心理
李宛 15级经济学
摘要:本文以丁玲女士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分析其时代意义,侧重剖析其所隐喻的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楚,同时对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与疾病隐喻进行了揭示。
关键词:莎菲,时代意义,Modern Girl,颓废文明,父亲,疾病
因为越轨的笔致与人物形象的颓废姿态,丁玲女士的诸多小说成为经久不衰的名作。往昔有幸与一、二友人品读《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时候的丁玲还没有在桑干河上,还没有进步成无产阶级战士,灵魂深处总有一抹柔柔的、淡淡的忧伤,一丝说不清楚的困惑,甚至“觉得他脸上的任何地方都适合放上我的吻”。一友道:“最美的女孩子,应该是最像女孩子的女孩子。”诚然,虽然这本小说是女性残忍文学的鼻祖,也是男性世界里女性的痛苦表达,然而莎菲表面的反复无常神经质,实际是那一代人找不到生命重心,寻求突破重重生命困境和颠覆传统的生命体验的一种戏剧化的可爱的表现。而丁玲笔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莎菲”型女士,不仅可以认为晚期的作品《在医院中》是“莎菲女士在延安”,《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莎菲女士在霞村”,甚至可以认为早期一系列作品主人公都是莎菲女士在不同环境下的灵魂初级版本。本文主要从丁玲笔下的莎菲型小说的正、侧面进行分析,解读这一组莎菲群像中所蕴含的颠覆男性——女性这一传统性别对立的精神自卫姿态,现代女性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深层觉醒和对废驰社会中自我灵魂的激情透视。
一、正面分析:时代意义
“一个女人,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无法得到同性的尊敬”,[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当女性失去自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时,她们就只好通过被男人的爱来确认自己。而“爱”这个字眼究竟代表什么?是蹙烟眉下的暗流,还是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出自《国风·卫风·伯兮》,全诗表达思妇的思念之苦。]或是到黄昏,点点滴滴?心碎于你,即是爱情,它仿佛是禁忌般的不可被提及。曾有多少人在爱人的怀抱里沉湎,却被耳鬓厮磨间一个呵气如兰的“爱”字惊得幡然醒悟,失措般地要挣脱那双钳在自己腰间的大手,隔着单薄的衣服感受那温实而欢愉的悸动。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告诉亚当,这是你的妻子,她必将从属于你。从此,人世间便有了爱情,千百年来如此。在爱的名义下,女人心甘情愿地做着男人的附庸和奴隶,为他伤心,为他欣喜。然而,奴隶也有不自由、不情愿之时。所以,世界上有了莎菲,肺病,饮酒,伤感春秋。那么多小女儿家心思,那么多柔柔弱弱细细思度,减了玉肌瘦了心肝。所以说,这就是女人?
然而莎菲绝不仅如此,她从现代人的自主意识出发,在爱情寻求中并不寻求被爱,这一不平等的单向索取模式中女性成了被占有的对象,从而消融了自我。她所要求的是在两性间的平等互爱中求得充分的自我实现。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在莎菲构筑的新型两性关系中,女性不仅仅充当男性的审视对象,她们也有权利把男性视为自己的审视对象,在相互审视选择中维持男女双方的平衡。
1.1自我主义
莎菲不仅“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折磨”真心挚爱她的苇弟,主动挑逗凌吉士的色欲激情而最后又逃离,而且对好友同学也缺乏信赖:“剑如既为我病,我倒快活,我不会拒绝听别人为我而病的消息”。自我主义使莎菲陷入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深渊中,也使她反省自己的本质。然而,莎菲无法走出自我主义的迷途,她反感人们的指责与不理解,结果与人们更加疏远了。莎菲视快乐的源泉为“糟蹋”,却无视生命伦理与人生道义的自然规定性。因此,莎菲作为首次出现的自我主义的现代女子形象,鲜明夺目得让社会与文坛惊讶,她既背叛了封建传统又不同于五四启蒙主义,成为现代都市颓废文明的文化象征。
1.2隔断传统家庭
男权社会派定给女性的归宿是家庭,这一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五四”第一批推出的女性启蒙者所要挣脱的不是家庭本身而是冷酷家庭,所要寻求的不是女性的彻底解放,而只是一己能够得到起码尊重的温馨家庭。
而丁玲笔下的女性对家庭缺少那样的兴趣,更谈不上归宿感。退职太守送女儿梦珂到上海读书,是为了重振家声,而梦珂则梦想开阔视野。她曾有过朦胧的爱情,梦境幻灭后便不再对爱情与家庭抱有希冀,而是投身于演艺界中去;已经涉足爱河的莎菲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并不以婚姻家庭为目标,而只是想咀嚼爱的体验,品尝女王似的甘味与上位的权威。重视家庭的传统与隔断通往家庭之路相较,后者更具反抗色彩。
1.3彷徨中抗争
相较于古代女子的毫无人格自由而言,莎菲们受到高等教育这一幸运,反倒是一种更深沉的悲哀,这源于有知有识的女性受男性文化传统教育的灌输更彻底,受其影响更深刻,她们虽然有了更深层的觉醒,却又无从寻求到一条理想的解脱之路,这样一种无奈和困惑的窘境把她们牢牢圈住,窒息了情感审视和生命体验。她们一时扮演着反传统、反封建的先锋角色,一时又失落于毫无未来的现实价值中。作者虽无力为自己笔下的人物提供明确的社会理想,指出具体的新生道路,但又决非是安于感伤中而不能自拔的,而是在无力的抗争中上下求索,在生命的荆棘中艰难前行。进退两难的莎菲们在饱受尴尬、迷失之苦的同时,亦艰辛地体味着这叛逆绝叫之后的勉强解放的自我,梦醒以后的无路可走驱使着她们不得不寻求自我解救的精神支撑。
1.4性爱道德的双重性
1.4.1身体自由支配
在丁玲作品的性爱世界里,女性的身体只对自己的感情负责,只要情有所钟,便不惮于罔顾一切的奉献,情丝扯断,也对曾经的给予无怨无悔。在《一九三O年春上海》中,玛丽沉溺在她与望微初恋中的温馨之梦,待到分道扬镳之时她也毫不自责,而望微也在痛苦之后付以理解与祝福,没有丝毫道德上的蔑视;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让人们惊讶的是,莎菲对异性的渴慕不是崇尚高尚或精神爱慕,而是对男性色欲无法控制的冲动与癫狂。当莎菲希望凌吉士“只限于肉感”、“用他的色”来摧残她的心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无法像别的女人那样承受而决定离开。在这种意义上,莎菲不同于五四时代的“叛逆之女”,后者追求的是爱欲的权利与爱欲的高尚、纯洁,而前者却把情欲投向生理意义的男性色貌,人生经验使她明白“爱”隐藏的生理欲望,使她怀疑和不敢接受人间的爱情。因此,莎菲无法抗拒“色欲”而招致的人格堕落,仿佛不是对都市色欲世界的谴责,而是对生命强烈色欲的经验与认同,昭示一种另类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诞生,即在女性解放和都市文明的历史合力中滋生的“颓”与“荡”之盈盈气息。
而与觉醒解放的女性相反,《夜》里的有妇之夫何华明分明感受到了有夫之妇侯桂英的青春活力与柔情蜜意,他“讨厌她,恨她,有时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在那个半个月亮倒挂山顶上边的夜晚,当侯桂英来到他身边,牙齿轻轻地咬着嘴唇望着他时,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欲念,他本可以无所畏惧地去做那件侯桂英热烈期待而他也未尝不愿的事情,然而他忽然被“另一个东西”牢牢攫住,冷酷地推开了她。那“另一个东西”恐怕还是根深蒂固渗入骨髓的封建贞操观。这是一个强烈的反讽:本来最受贞操观压抑束缚的女性觉醒了、解放了,而男性却萎靡不振、龟缩回去。半个月亮爬上来,光辉熠熠的是女性,而男性还在用所谓事业的辉煌掩饰着人性的阴影。
1.4.2精神渐趋独立
但另一方面,丁玲对五四之后女权主义者的性解放进行了降温处理,彰显了女性的胜利不在于肉体彻底解放而在于其精神之独立。当莎菲认清自己对凌吉士不属于真正的爱情时,她一方面在心里叫喊“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同时又“用力推开”。在偏激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像男性征服自身一样去征服男性的身体,就是女性最终的胜利。而莎菲是否认那种对男性身体的征服权欲的,她扭转了一直依赖身体的征服说法,希图真正的爱的融合。那一推,就让莎菲和整个虚假世界作了分离,完成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历程史,丁玲赋予了一个女性最后的醒悟,然而真实的生活中又有谁为女性明智地做个决断呢?这也正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最大表现。放弃苇弟,也拒绝了凌吉士,莎菲没有在那两个男人之间完成女人的性幻想和性实践,不是她得不到,而是她对自我的超越,成长为脱离了性的爱情的干净、纯粹和成熟。她深味通透了所谓的性,也告别了性在传统意义上的论断和界定,赋予了女性意识里性爱道德的新含义。
1.5囿于时代的颓废二态性
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的时间——一九二七年,是大动乱的一年,知识青年迷惘于社会现状,但又看不清未来前途,而所谓的Modern Girl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下产生出来的,反映在丁玲创作的女性姿态中,就是对于生的厌倦而又不得不生的苦闷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莎菲女士被某些批判者指斥为“玩弄男性”的恋爱至上主义者与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与道德颓废的化身。这种批评实在是既不懂女性心理又与文学本性隔膜的谬见。
首先,针对“恋爱至上”,不必讳言,她是有这个方面的萌芽的,因为她是那个时代处于极端的苦闷、焦躁、仿徨之中的Modern Girl的典型。然而社会苦闷与性苦闷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肺病的折磨,使性爱追求成为当时莎菲几乎唯一的寄托。可是一个可靠而不可爱,一个可爱而不可靠,并且那可爱也因了灵魂的卑劣大打折扣,她的理智要她鄙薄这颗包藏在那臭皮囊下的卑污的灵魂,她的感情却叫她享受那漂亮迷人、体魄强健的肉体,她处于极端的矛盾当中,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小说像《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如此精湛卓绝地描写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一个少女为爱情、为情欲苦苦挣扎的心理,那样伤感,那样苦闷,又那样炙热,那样痴迷!因此,莎菲反感于那种完全是为了满足性欲而出卖感情的庸俗,她的恋爱观并不是纯粹基于对肉欲的一味追求。既然莎菲无法爱恋迂拙的可靠,也无法拒绝美丽的诱惑,因而她还要继续品尝选择的苦味,这种自啮其心的咀嚼苦痛与所谓“玩弄男性”绝非可以贸然对等。
而这种对于Modern Girl的独到描写,也正是丁玲的天才之处,是五四女性作家所不曾有的新姿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莎菲简单视为叛逆封建旧礼教、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是遮蔽了小说真实的文学意义,削弱了它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不能取代的典型意义。可以说,丁玲塑造的莎菲形象不仅标志五四女作家的创作进入新阶段,而且标志作家对都市青年“经济苦闷”与“性苦闷”的表现转向对都市女子放浪行为的表现。
其次,“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与道德颓废的化身”这样的批判也实在是过于苛刻。莎菲像孙舞阳[ 茅盾《动摇》中的灵魂人物,美艳动人,是有妇之夫方罗兰的迷恋对象,招摇、热情、随性,是官太太、官小姐眼中的异类。]等Modern Girl一样,有着现代都市颓废文明的特征,但莎菲与她们的差别有两点:第一,她的渴望与幻想发生在孤独的房间里,不像孙舞阳们的行为发生在大街、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因此,莎菲们虽深处Modern Girl的典型生活的核心,但还不是完全资本主义化的,“找不到最富丽的新装,看不见不断变幻着光色的跳舞场,也看不见金醉纸迷的大宴会;同时,也没有家备的Moter car,自动的电话机,金刚钻,画眉笔,以及香槟酒”。[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二,莎菲为情欲而发狂的同时,还谴责自我的堕落并鄙视凌吉士丑陋的灵魂,心理与行为矛盾混杂,既渴望、追求情欲的满足又厌恶这种颓废,既心甘情愿地沉沦又谴责自己的堕落,既隐含现代颓废文明的气息又拥有现代启蒙理性的精神气质。总之,莎菲的苦闷并非仅是灵与肉的心理冲突,还隐喻启蒙主义与颓废主义的文明冲突,象征着启蒙主义遭到颓废文明侵袭与挑战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苦。因此,莎菲的审美意义,既不是反抗封建传统的五四性质的现代女性,也不是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完全摩登化的都市女子,而是一个启蒙文明向颓废文明衍变中的遗留产物,既时髦又守旧的文化心理造就了她的混杂特征。
但是,部分评论者质疑过度解读丁玲。诚然,文学阅读大可不必过多的史学阐述而损害生命关怀的重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丁玲不是从所谓的政治社会中取得妇女解放权利的观点出发,她本身也不一定充分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具有和人的精神感性最深奥的自由解放问题的自在联系。就像反抗欺凌女模特的老师的梦珂恐怕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在与整个男权社会抗争。她的不满,是对男权中心的社会的不满;她的屈辱,是封建势力施加的屈辱;她寻寻觅觅,到处碰壁的艰难,是知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闯荡的艰难。因此,我们不可否认作家以一个新女性的身份塑造其女性形象的折射效果。
二、侧面探讨:父亲形象与疾病隐喻
2.1父亲形象
丁玲塑造的一组莎菲型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以对父亲的依恋为透视点,从一个侧面来探寻并完善中国现代女性的精神建构。
应该说,对父亲的依恋产生于莎菲们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起点往往便是一位送行的父亲。虽然,父亲之于离家漂泊的女儿,不过是这样一个起点上的瞬时存在,但女儿对父亲深切眷恋,并在无母的伤感中,更添相依为命之感。不过,这个情结始终是隐秘的,它藏于文学史上充满捐傲雄强之美的莎菲背后,与之不相谐和,透出怀旧的温柔和伤感。由此,莎菲正面体现的现代意识与其背后隐士的传统眷恋,便形成了一系列有意味的反差和对照。男女性别虽然是自然法则所分立,但其固有的特质往往包含着内在深沉的联系。因此,莎菲们反映的是女性对社会和男权的反抗,但是另一方面,她们的背后同样蕴藏着对父亲即男性的依恋和寄托,尽管这种依恋和寄托是女性意识中潜在的渴望。
因此,丁玲笔下的莎菲们还没有完全成长为具有充分、健全的女性自我,尚处于走向独立人格中的萌芽期。但是,较之于五四同期的新女性,莎菲们所达到的现代精神的高度处于绝对超越地位。同时,丁玲突破了女性人物形象绝对女性化的文本建构,没有死板地囿于反封建的口号,而是让男、女两性在其创作中一直互为参照,并且把这种参照纳入到了现时的社会环境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2.2疾病隐喻
莎菲的疾病在表达其“创伤”时,更是负有特殊的使命和意义。在论及疾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内涵与意义的时候,当代美国著名作家及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所著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疾病“表达了一种人们对事物不满的感觉”;“疾病是通过身体说话的个人意志的表现,它是展示内心世界的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形式”。[ 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 York:Picador USA,2001),pp.44,73.]
2.2.1背离社会
“任何形式对社会规范的背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病态”。[ 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 York:Picador USA,2001),p.56.]巧合的是,在丁玲的诸多小说中,几乎所有女主人公都同样经历了背离传统社会及试图打破传统女性角色的过程。无论是莎菲、梦珂还是阿毛,当她们试图遵守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生活时,她们就抛弃了女性自我,面临着自我崩溃;而当她们违反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时,她们就陷入病态。面对不利的环境因素,莎菲们都作了各种努力和挣扎,试图摆脱她们的不适、忧郁和焦虑,更重要的是,要挣脱外部力量所强加于她们的传统女性角色。
2.2.2唤醒情欲
疾病与女性情欲世界也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苏珊·桑塔格指出,肺病具有情欲催化作用,往往会使情欲加剧,并且能产生巨大的情欲诱惑力。[ 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 York:Picador USA,2001),p.13.]莎菲潜意识中意识到病痛对身体的影响,身体上的病痛用于建构矛盾的、但却是欲望着的自我。最终只有通过真正了解她的情欲世界才能进而理解并得以建构一个真实的自我。其实疾病与情欲的联系从日记一开始就可捕捉到,当她抱怨她面对着压抑的天花板以及四堵难以逾越的墙壁时,一方面是在表达总体感觉,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描述久受压抑的欲望情感。疾病的症状如咳嗽、失眠和厌食,都可以看作是对被压抑欲望的一种加了掩饰和伪装的表露。正如在与蕴姊相处中,莎菲利用她的疾病寻求宽慰关心。从莎菲在情欲的绝望挣扎中可以看出,她对自我的认识并不是从自身得以印证的,反而是从与凌吉士的交往中发现的。她的自我不仅与凌吉士的传统人格相拒斥,而且在情欲世界也同样无法得以融合,反而通过情欲世界的隔膜最终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
2.2.3死亡
疾病不仅与内心矛盾有关,同时也与死亡欲望发生关系。其实,当莎菲于病中痛饮之时,她实际上选择了倾向于主动寻求死亡,试图用肢体行动来改变思想意识,用毁灭自我的行为来调节失衡的矛盾心理。死亡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地驱除欲望和矛盾的同时,也可以使莎菲最后一次控制自己、最后一次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为女人,丁玲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也更懂得她们的痛苦,莎菲型的矛盾女士是丁玲笔下女人形象的成长痛苦与自我完善,这也是丁玲自己人生的写照。尽管笼罩在巨大的悲剧感里,却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女性自我的唤醒,这启示我们新一代用自我的还原坚持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 刘文.《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身体意象解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2):111-115.
- 蓝棣之.女性的愤懑和挣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解读[J].贵州社会科学,1998,(4):66-74.
- 王烨.莎菲作为“Modern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EB/OL].http://www.docin.com/p-939460245.html,2017-12-10.
- 杨姿.被背叛的解放——丁玲笔下的莎菲悲剧解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6):258-264.
-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Sontag,S.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M].New York:Picador USA,2001:13,44,56,73.



 loading......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