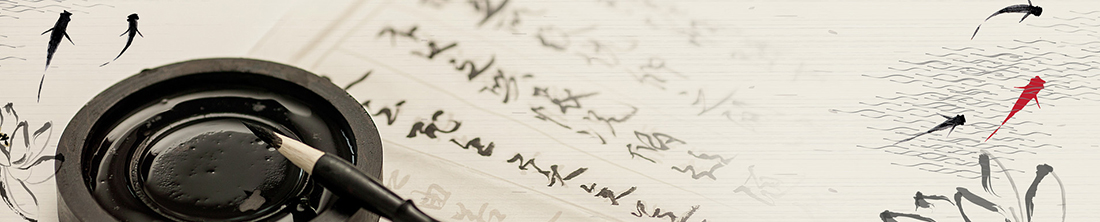
冰冷的手术刀——《围城》文笔风格小探
郦捷 14级化学
【摘要】在钱锺书的《围城》中,精彩的修辞与辛辣的讽刺风格显然是使其广受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作者借助其文笔风格所传达出的思想内涵——对人性虚伪与社会丑恶的批判,以及对“围城”心理的哲学反思,才真正使得这部作品称得上伟大。本文从具体文字出发,对《围城》的文笔风格进行了简单评析,并分析了讽刺性语言对传达作品主旨的作用。
关键词: 《围城》 文笔风格/语言风格 修辞 主旨
钱锺书的《围城》自从问世以来,便以入木三分的讽刺和惟妙惟肖的修辞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语言风格最为奇特的一部作品。许多读者被这部小说深深吸引的第一原因便是作者酣畅淋漓的幽默文字与跳脱于常人思维的精巧比喻和联想[1]。杨绛在读《围城》的手稿时,钱锺书急切地等待看她的反应,而她也总是不能自已地发笑。(“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钱钟书与<围城>》杨绛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p209,下省略书刊,仅示页码)然而,这部小说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留学生群像的细腻描绘以及对“围城”心理的哲学反思使其不囿于卖弄语言而得以成为一部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作品。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围城》辛辣而又深刻的批判与讽刺意味也是通过其独特的文笔风格实现的。讽刺的语言是冰冷的。钱锺书在写作时对书中的任何人物与非人的事物从来都不留任何情面,而这正像是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将一群人、一个社会解剖开,揭示出其病态的本质。
要说《围城》中最为鲜明的语言特点,必然是新奇而富有想象力的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在一部只有二百多页的小说之中,仅仅比喻手法就使用了多达七百余条,三百五十多处[2]。这样密集的比喻运用,读来应接不暇,有如享受一顿天才想法的饕餮盛宴,着实令读者过瘾。而这些修辞又相当完美地承载了钱老希望借以抒发的讽刺意味,铺垫了整部作品语言风格的基调。就拿书中对几个人物初次亮相时直接或间接的描绘为例:
“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p3)
这是对小说开篇在回国船上“勾引”方鸿渐的鲍小姐的一段精彩万分的描绘。鲍小姐的穿着在那些男学生口中竟成了“熟食铺子”,寥寥四字便将鲍小姐衣着的暴露以及在此情此景下的不合体统刻画到位。而之后“局部的真理”这一称呼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局部”这两个字的点拨反而令读者更加浮想联翩,哑然失笑。钱老深厚的语言功力,在此可见一斑。
另一处对人物形象的典型刻画,是对陆子潇样貌与五官的取笑:“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为帽子埋没, 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傍横溢。”(p121)这两处对于头发与鼻子的联想可谓精彩绝伦,超脱了绝大部分作家想象力的水平,简直可谓嘲讽到了极致,读来却是妙趣横生,令人拍案叫绝。
书中对人物形象的讽刺也不仅限于外貌层面。对人物思想、言行的挖苦讽刺,则更增强了其批判的力度。在提及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之时,钱锺书还不忘对他“老科学家”的身份玩弄一番——“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不大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p114)钱老怕是觉得直接称呼高松年为“老科学家”实在是有点太抬举他,因此先行指出这一称谓也可以作贬义解,让读者有一些心理准备。而在此之后对于高松年耍各种手腕以满足自己膨胀的政治野心的行为,也就与其人物形象更为相称了。
然而在《围城》之中,作者是否对所有的人物都冷嘲热讽了一番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方鸿渐所真正爱恋的女孩——唐晓芙的描绘,钱老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而没有采用带有讽刺意味的字眼:“(唐晓芙)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 (p29)除此之外,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赵辛楣这一人物,钱老也显得比较留有情面。究其原因,在于语言手法作为一种传情达意的工具,终究是要为文本的思想内涵服务的。在这部小说形形色色的人物中,他们引人“厌恶”的层次也是不同的:方鸿渐父子与赵辛楣多少还是保有了一些底线,他们的“丑陋”基本无伤大雅;苏文纨、陆子潇的虚荣最多算是庸俗可笑,也不至于让人恨从心生;可韩学愈以假文凭博取教授职位的行为就属于一种市侩的欺诈,可谓人人得而诛之了[3]。因此对于不同的人物,作者进行讽刺的力度也不同,是非评判便通过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涵括在了语言之中。这正如手持一把解剖刀,可以蜻蜓点水,点到即止,也可以开膛破肚,寻根问底。钱锺书操着这把语言的手术刀,剖开了人物言行这层迷惑性的外衣,将人性的复杂与丑恶冷酷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除此之外,钱锺书的冷笔也有数次留下余地,宜时即收。如下文中刻画李梅亭暴躁的性格,只考虑个人利益却全然不顾他人死活,则将全部着墨都限制在了李梅亭身上,而没有顺手一笔去嘲笑车夫:
“走不上半点钟,有一个很陡的石子坡,拉李先生那只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收脚不住,摔了一交,车子翻了。李先生急得跳下自己坐的车,嚷:‘箱子给你摔坏了,’又骂那车夫是饭桶。车夫指着血淋淋的膝盖请他看,他才不说话。好容易打发了这车夫,叫到另一辆车。”(p89)
就凭钱锺书那能够笑天下万物的能耐,车夫这血淋林的膝盖想必也是作为笑料的绝佳素材。然而钱锺书在此做到了适可而止。如若他也信手将车夫纳入冷嘲热讽的范围,那就像是丧礼上开死人的玩笑,笑而不得其所,从而招致读者的反感[4]。而一旦读者不再欣赏钱锺书这一独特的语言风格,辛辣的讽刺就不再是一把解构社会与人性的手术刀,而成为了日本军人用来切腹自尽的武士刀。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钱锺书的艺术成就,其精妙绝伦的语言风格,实际上也是与他的文学造诣分不开的。钱老写方鸿渐寄给家里“悔婚信”:“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p4)用词十分怀古,颇具文学意蕴,同时也透露着钱锺书深广的文化内涵。事实上我们对钱锺书的文学背景深入考察一番,便不得不惊叹他的文学造诣之深厚。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依然潜心于学问研究,创作了《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经典的学术著作。而他博通古今,才贯东西,也为他作品的熠熠生辉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5]。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洞察力使得他的文字作品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也令人不禁感叹于他的才俊。而离奇的想象力则使语言的魅力更上一层楼。譬如他写苏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他把客堂里的书画古玩反复看了三遍,正想沈子培写‘人’字的捺脚活像北平老妈子缠的小脚,上面那样粗挺的腿,下面忽然微乎其微的一顿,就完事了,也算是脚的!”(p28)完全超脱了对于书法作品评价的常见角度,用一个出乎意料的比喻联想,创造出了一种非常值得玩味的审美意趣——一是对苏文纨的实际艺术欣赏水平不动声色的嘲讽,二则体现了方鸿渐等待苏小姐时的不耐烦心理,真可谓是神来之笔!
嘲讽是《围城》这部作品基本的语言模式,但相较于我们常说的“冷嘲热讽”而言,或许是“冷嘲冷讽”显得更贴切些。《围城》中所写之人都是社会上的丑角。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产生的是一种“审丑”的艺术体验[6]。如何将社会上的丑恶以一种能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作者的写作风格与立足点都具有极高的要求。钱锺书自始至终采用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过分地将自身的热情或急切的期盼投入到写作过程中来——而这正是通过他独特的、嘲讽性的语言风格实现的。《围城》中的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这个时代的中国,就是一副混乱、肮脏、疯狂的图景。而同样是描写这样一个时代,沈从文笔下《边城》所展现出来的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就仿佛产生于另一个世界——有星光月影的美妙画卷,有婉转悠扬的浪漫歌声,有泥土的芬芳与山果的清香。沈从文书写时用的笔是带有颜色和温度的。他在一个特殊的战乱年代创造了华夏大地中的一方净土,并希望借此重新唤醒人的美好本性。而对于钱锺书,他写作用的不是笔,而是一把冰冷的、毫无温度的刀。他所写的是残酷的现实。他面对着一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不动声色地将之缓缓剖开,展现出病入膏肓的脏器以警醒健康的、有良知的读者。钱锺书竭力用幽默的语言来冲淡读者内心感受到的不适,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掩饰或是美化丑恶时代下丑恶的人。要做到这一切,不仅需要有高超的文字功力,更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心灵。我们无法简单地评论《围城》与《边城》哪一部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但《围城》所揭露的社会现实,其深刻的批判意义显然来得更直接、更痛快,也更容易使人产生心灵上的震颤。而这一切,都是借助于《围城》无处不离讽刺的文笔风格实现的。
试想一下,如果这部作品中不再有铺天盖地的嘲讽,而是带着如火般的热情去描绘同样的故事与人物,整部作品的批判力与思想性也必将大打折扣。不将曹元朗引以为傲的“大作”《拼盘姘伴》公之于众,怎能令读者体会到所谓“新诗人”的真正文学水平有多么可笑?不把高校长掌控三闾大学的种种手段写得老奸巨猾,怎能深刻地揭示出这位“生物学家”以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之名行封建与个人崇拜之实的荒诞?由此观之,钱锺书从头到尾的冷嘲热讽,绝非贪图一时口舌之快,而是为了借此传达出他对书中人物的思想态度。因为《围城》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本身就值得讽刺。只有通过讽刺,他们的人物形象才变得丰满具体,而钱老对文化、对人物、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才得以凸显。在此之中通过钱老的睿智所展现出的语言魅力,只是传达思想的一个附属品而已。即便如此,钱锺书奇峭的语言风格依然为修辞学的研究者带来了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
正如其他经典的文学著作一样,精妙绝伦的语言也需要为思想内涵服务,否则同样会沦为流俗。钱锺书的《围城》虽然能够凭其语言特色在修辞学上傲视群雄,但它对人性丑恶的揭示、对生存哲学的批判性反思才是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在文坛上经久不衰的原因。一把明晃晃的手术刀,可用来洞察病理,亦可用来医病救人。但若没有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生,它只会是一个不起眼的铁块。
【参考文献】
- 任玲艳.《围城》的比喻艺术[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2, 14(12):129-130.
- 卢斯飞. 意蕴丰富 韵味悠扬——钱钟书作品中的幽默[J]. 阅读与写作, 1994(6):16-17.
- 阎浩岗. 关于《围城》的文学史地位[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3(3):73-77.
- 黄国彬. 几乎笑尽天下——评《围城》的冷嘲冷讽[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36(2):99-106.
- 柯灵. 钱锺书的风格与魅力——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J]. 读书, 1983(1):24-29.
- 隋清娥.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116-120.



 loading......
loading......